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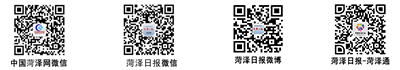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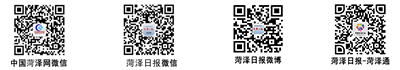
作者: 來源: 牡丹晚報 發表時間: 2025-06-30 09:44
“彩云之南裕華村”先生:
感謝您對我小詩的解讀。您對我的《芒種》的解讀,確乎有知音之感,仿佛獨行荒原,終得回聲。嚶其鳴矣,求其友聲。
您對詩學特別精通,您從《芒種》詩里,從我的文字背后,深刻觸及了現代性困境的本質。節氣在現代,在高樓林立的“后農業時代”,其符號意義已轉化為某些有思考的現代人精神隱喻的載體,其中揭示的,正是數字時代、AI時代人與存在根基、人與大地的斷裂。我就是一個“紙上行走”的人,在信息繭房圍困的現代,這不是孤立的個人形象,而是一代人的縮影。我們在虛擬世界構建意義,卻在真實土地面前失語,這種“圍墻里的呼吸”,本質上是生命體驗的悲劇。
您提到的“語言焦慮”深獲我心,“當我沉默著的時候,我覺得充實;我將開口,同時感到空虛。”如何表達現實的困境?我對語言是懷疑的,當文字成為刪除與重建的循環游戲,當“多余的饒舌”暴露出表達的虛妄,寫作本身便成了荒誕的劇場表演。這究竟是“指尖生了銹”,還是“大地養了蛀蟲”?
我真是懷疑思維思想還有語言,或者詩歌的合法性與有效性。在技術異化的時代,一個詩人何為?一個詞語何為?但這種病灶并不能解除我的疑惑,也許詩性可以稀釋這種困境。
感謝您對“反節氣詩”的定位。我是一個農村出生的人,在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帶,對農業社會有很深的情感。但是,現在的詩歌,必須面對我們不再是傳統的田園牧歌,我們的文字不應再是傳統農耕文明的節氣敘事,充滿豐收頌歌,而應反映我們走出農耕,走到精神荒原的真實心態的自白。在AI寫作、虛擬體驗泛濫的當下,詩人又該如何面對“播種與收割”?
我們也在播種,但不是在大地之上。如何“觸到大地脈搏”?這不僅是我的焦慮,亦是許多人的焦慮。如今我們看一下夕陽,看一下地平線,踩一下泥土都成為奢侈。我們渴望文字的堅實,我們又懷疑文字的虛妄,這也許就是我刪除的文字的內在考量。我們渴望現場,渴望在場,這也許就是當代人的困境的精神芒種。
讀過您對《芒種》的解讀,仿佛在文字的阡陌間遇見了另一位深耕者,在詩的土壤里挖出了現代性困境,您關于存在疏離、語言焦慮與時代病灶的叩問,與我的詩產生了新的共振。
我詩的結尾“指尖生銹”與“大地蛀蟲”并置,您解讀為“個人責任與時代困境的兩難”,這一洞察令人感佩。在我看來,這不是非此即彼的質問,而是您指出了很多當代人面臨的困境,當一個寫作者懷疑自己“從未播種”時,何嘗不是在揭露“大地”已被不可描述的勢力、乃至資本、技術等“蛀蟲”啃噬得不再適合耕耘?正如工業化農用化肥導致大地板結,農藥令食物失卻本真。
荒原之上,仍有微光。云南邊陲的裕華村與我在中原地帶里書房的寫作,看似相隔千里,卻共享著對“真實”的渴望。您讀懂詩中的土地記憶,我在鍵盤前試圖用文字復現一個麥穗,這本身就是一種跨越時空的“芒種”實踐。感謝您的厚愛,這不是“一個節氣的詩”,而是“一個時代的寫照”,但每個在寫作中堅持叩問的人,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為荒原播下意義的種子。
讀您的賞析,讓我意識到“芒種”的本質從不是二十四節氣表上的刻度,而是一個持續的動作,是農人彎腰插秧播種收割與土地的對話,是一個寫作者刪除文字后對真實的逼近,更是每個現代人面對虛擬與現實的隔膜中,堅持用身體感知世界的姿態。
愿我們都能在各自的“芒種”里,既不困于紙上的行走,也不淪為大地的看客,做一個所謂“憫農者”或看客自了漢。我們深知,畢竟真正的播種,從來發生在指尖觸到土壤、呼吸混著麥香的時刻。
大地之上,有我的父老和家園,也有我的精神歸宿。
再一次感謝您對《芒種》的解讀。詩歌何幸,遇到解人。我等何幸,求其友聲!
此致
夏安
黃凌霞
2025年6月16日
 魯公網安備 37172902372011號
魯公網安備 37172902372011號